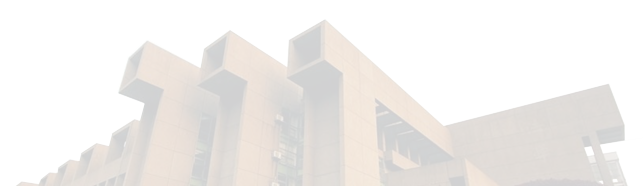转自政法论坛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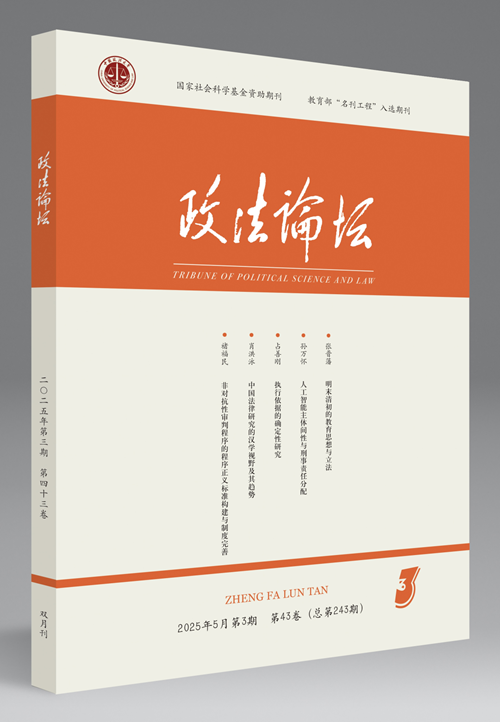
《政法论坛》编辑部首发
编者按
为了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创新期刊传播形式和方法手段,有效发挥期刊在学术质量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加快融合发展、提升国内国际传播能力,推动学术期刊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升级,《政法论坛》秉持创新发展与严格把关并重的原则,探索实施网络首发制度,从2022年第1期于中国知网陆续推出网络首发文章,并于政法论坛微信公众号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中国法律研究的汉学视野及其趋势
肖洪泳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拟发表于《政法论坛》2025年第3期
摘要:西方汉学最初大多局限于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进行介绍,其对中国法律的研究起步虽晚,但是日渐深入和成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汉学,已将中国法律研究加以深度垦殖,优秀学术成果节节攀升。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与德国是中国法律研究的中坚力量,涌现出爱斯嘉拉、宾格尔等汉学大师。20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的研究中心由西欧转向北美,美国成为中国法律研究的执牛耳者,欧洲的法国、德国、荷兰、英国仍不甘落后而各有所长。21世纪以来,美国继续肩扛汉学领袖的旗帜,并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推动下,将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的各自优势予以整合,将中国法律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研究人员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20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的中国法律研究都经历了一系列新变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以及中国学者对外交流与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汉学的中国法律研究必将得到深入推进,从而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来自异域的他者视角,促进中国法律研究及其实践的繁荣和进步。
关键词:中国法律研究;现代西方汉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亚洲法律研究中心
目录
引言
一、20世纪上半叶:专业汉学兴盛时期的中国法律研究
二、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引入阶段的中国法律研究
三、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全面渗入时代的中国法律研究四、结语:中国法律研究的汉学趋势
引言
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以及早期的专业汉学,西方汉学由于大多局限于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进行介绍,因此特别注重于中国的人文传统阐释而对法律等方面的社会科学问题着墨不多,即使偶尔谈到法律问题,一般也都会跟政治控制、礼教风俗之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葡萄牙神父班尔西奥(P. Belchior)于1554年就将一些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编写有《中国的风俗与法律》一书,但并没有对当时中国的法律进行过多的介绍。就是到了18-19世纪专业汉学开始抬头的时代,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观。即使19世纪中后期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牧师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为根据,撰写了《中国:法律、风俗与习惯的历史》一书,用较长的篇幅记述了中国的司法程序以及刑罚问题,颇有精彩之处,但仍将法律问题与风俗习惯联系在一起,而且颇多错误和不足。长期旅居中国、并受李鸿章派遣任职朝鲜的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撰写的《中国婚姻家庭法》,也基本上停留于礼俗与礼制之类的介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运作本身就受制于政治与伦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西方汉学的主要研究者都是传教士,他们当然还不会单独对中国的法律问题青睐有加。但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的《中国丛报》,为了向西方国家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情报,通过长达20年左右的办刊,对当时中国的政制、刑事法律和诉讼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而集中的介绍,反映出了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这对后来西方汉学日渐关注中国法律问题以及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法律进行专业化的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汉学日益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现代西方汉学开始将中国法律尤其是中国传统法律或中国法律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加以深度垦殖,取得了丰沛而优秀的学术成果,呈现出一种中国法律研究的崭新视野与趋势。
西方汉学这种学术视野素来也为中国学界所密切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更加关注西方汉学的进展,开始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译介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除了翻译出版汉学著作,中国学界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研究》《外国研究中国》《美国中国学手册》《欧洲中国学》等文献信息工具书,并推出了一些汉学刊物,如《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汉籍与汉学》《法国汉学》等。随着西方汉学译介过程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法学界也逐渐注意到西方汉学有关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认真加以对待。但是目前中国法学界对西方汉学有关中国法律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发展脉络仍然缺乏足够深入的认识,尤其相比于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汉学在这一领域全面繁荣的研究格局而言,我们迫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法律研究的汉学视野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他者视角,这对中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或参考意义。
一、20世纪上半叶:专业汉学兴盛时期的中国法律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现代西方汉学开始步入专业汉学兴盛时期,尤其是有关中国法律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传教士汉学所存在的局限,涌现出了一些既精于法学又长于汉学的研究专家以及有关中国法律研究较有影响的汉学著作。首先从研究阵营来看,这一时期欧陆的汉学家是中国法律问题的主要研究者,法国和德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主力军,特别是法国的爱斯嘉拉(又译为埃斯卡拉,即Jean Escarra)与德国的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都既是法学家或学习过法律,又是汉学家,代表了当时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最高水准,此外马伯乐(Henri Maspero)也于大学期间研习过法律,尽管其主要致力于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宗教方面的研究,但在法律史领域也发表过一些很有分量的作品。其次从研究领域来看,这一时期西方汉学主要集中于唐代与清代的法律问题研究,着眼于法律文献的梳理、翻译和解读,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有特点的研究主题。最后,这一时期的汉学家大多都在中国从事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对中国有着比较切身的经验感受,而且很多汉学家有关中国法律的著述都是用外文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的,爱斯嘉拉与卡尔·宾格尔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爱斯嘉拉曾为巴黎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也是20世纪前叶法国民商法和比较法学的巨擘,并于1921年至1930年在华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法律顾问,随后又多次来华。在担任国民政府法律顾问期间,他不仅参与了商法等法律的起草,还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研究上还是在当时中国现有法律体系的分析上都建树颇丰。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中国法律在西方的传播,曾经亲自执笔翻译梁启超的《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华民国1928年刑法典评注》等,并主编了法文版《中华民国大理院民商判例要旨汇览》(1912-1923)。爱斯嘉拉有关中国法律的论著颇多,除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问题有所关注之外,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介绍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律现状方面。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首推《中国法——概念和演变、立法和司法机构、科学和教育》一书,该书于1936年以法文分别在北平和巴黎出版,共559页。从全书的结构体系来看,爱斯嘉拉虽然主要是为了对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运作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介绍,但是也非常注重挖掘其历史基础,尤其是卷一有关中国法律思想的分析和论述以及有关法制沿革的历史追溯,大部分都参考了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以及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相关著作。此外,爱斯嘉拉还撰有《中国的法学与教育》《中国与国际法》《中国海事立法》《中国刑法典评注》《外国人在华租借制度》等系列著作,并发表过一些有关中国法律的论文,向西方世界广泛介绍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律制度与法律现状。
卡尔·宾格尔曾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图宾根大学,同时主修法学与汉学。他于20世纪四十年代前来中国,担任德国驻北平大使馆法律顾问并兼任上海多所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潜心于唐律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所著《唐法史源》一书,奠定了西方研究唐律的基础。该书于1946年由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以德文出版,引起西方汉学界高度关注,堪称经典。其中卷一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宾格尔首先对唐代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法律的特殊性、系统性和独立性都能够通过唐律得到较为纯粹的认识,而且唐代的法律文献能够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此外唐律也对日本、越南等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因此研究唐代法律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宾格尔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唐代法律的主要史料,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典籍或法典所涉法律史料,并特别对旧、新《唐书》与《唐会要》所涉相关史料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对自己选择翻译新、旧《唐书》的《刑法志》予以了说明。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宾格尔进一步讨论了唐代的立法体例与立法过程,尤其是律、令、式、格、敕等的编纂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然后又从法律渊源的角度对皇帝作为立法者、判决、习惯法、学说、经典典籍等在唐代法律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及其发挥出来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最后,宾格尔就律法对帝王大臣的约束进行历史考察,他认为这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儒法之争背景下“守法”观念的独特性质。此外,宾格尔还在当时法兰克福的《汉学杂志》上先后发表过有关传统中国法律对精神病患者及过失行为的惩罚以及有关中国人的习惯法即不成文法方面的学术论文,并把当时国民政府的民法典、商法典以及证券法、支票法都翻译成了德文,统合起来于1934年在德国马尔堡出版。
除了爱斯嘉拉、宾格尔这些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外,这一时期在重要法律文献的梳理和翻译上,古·布莱斯(Gui Boulais)译述了《大清律例》,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搜集和翻译了中国古代有关考试的法令以及唐代有关官员、军队的法令,也颇具规模和特色。曾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人阿拉巴德(Ernest Alabaster)所撰的《中国刑法释注》一书,也算当时《大清律例》的重要英文释本,他还在这个释注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法律与实践专门撰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另外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很多颇有特色的专题研究,特别是德国的汉学家可谓成果迭出。傅兰克(Otto Franke)先后出版有《中国土地所有制》与《中国治外法权》两部著作。安东·皮蓬(Anton Pippon)则以法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的奴婢制度》的学位论文,还将王世杰写成的《中国奴婢制度》翻译成德文专门附于文后,并于1936年在日本东京出版。英国的研究成果也不容小觑,阿拉巴德除了刑法释注方面的著作,还专门撰文讨论了中华帝国的法律官员问题。贾米森(George Jamieson,又译为哲美森)则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大清律例》以及《刑案汇览》中有关婚姻与继承的案例、会审公廨案例进行翻译和研究,最终在此基础上于1921年出版了《中国家庭法与商事法》一书,也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计划专攻唐代法律研究的荷兰汉学家何四维(Anthony Francois Paulus Hulsewé)因为听闻宾格尔已经出版了有关唐代法律研究的专著,遂决心放弃唐律研究而转攻汉律,但还是在1948年推出了自己有关唐代阶段性禁止死刑和屠宰动物的学术成果。另外清末的宪政改革与修律活动也受到了一些汉学家的高度关注,成为他们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譬如英国汉学家毕善功(Louis Rhys Oxley Bevan)著有《中国的宪政建树》,荷兰学者兼外交官梅耶(M. J. Meijer)著有《中国近代刑法导论》,分别探讨了中国近代的宪政改革及这一背景下的刑法转型问题,其学术意义也可圈可点。
二、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引入阶段的中国法律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因为特殊的国际背景尤其是两大阵营的对决以及冷战时代的到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不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典型代表与领导国家,其对中国的关注日显重要,从而加速了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步伐。作为美国最富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于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研读、旅行和教学,返美后长期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汉学发展和中国研究,甚至改变了西方传统汉学的研究范式与基本格局,导致汉学与中国学之争。因此这一时期西方汉学的研究中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同时在美国的影响下,整个西方汉学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中国法律方面的研究越来越获得汉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的高度关注,相关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节节攀升。总起来说,基于关注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传统的专业汉学已经无法满足这一学术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开始被大量引入现代西方汉学之中。
作为美国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学术带头人,费正清尽管对中国的法律问题关注不多,但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从制度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是出于这样的学术意识,费正清编选了《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一书,尽管还跟法律专题那样的学术研究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对后来美国汉学的中国法律问题研究无疑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不仅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连接了起来,而且也看到了思想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其在传统专业汉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汉学研究的一些新元素。从20世纪下半叶前期来看,美国汉学家大多都是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从法律思想或法律观念的角度着手中国的法律传统研究,譬如史华慈《论中国的法律观》一文就对典型的儒家法律观念进行了探讨,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讨论过法家以及“刑名”的含义,还专门研究过申不害,其中大量问题都牵涉到法律思想尤其是法家思想方面的阐释。这种研究传统在美国汉学界一直得以保留和发扬,后继者不乏其人。安乐哲(Roger T. Ames)与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长期合作撰写的很多著作都或多或少阐释过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特别是《通过孔子而思》一书比较深入探讨过中国古代的自然法观念以及耻感与罪感问题,他个人的独著《中国古代的统治艺术——〈淮南子·主术〉研究》则更是专设一章“法”,就先秦政治哲学中的“法”与《主术》中的“法”进行了一次宏观而不失深刻的思想考察。
但是相比于传统的专业汉学,美国的这种中国法律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中国进行解释,而是具有了一种反思现实中国的强烈意识。因此作为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的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虽然不再接受费正清“冲击—回应”的中国研究模式,转而注重从中国自身这一内部视角研究中国问题,但在连通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思想与制度这一学术立场上,却将费正清的思想主张运用到了极致。他在20世纪80年代着手研究和撰写的《叫魂》一书,虽然不是一部纯粹的法律史著作,但却详尽无遗描绘和分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机制,而且他自己在撰写中译本序言时也明确说到,《叫魂》赖以利用的那些文献档案“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在全书最后两章的理论反思中有着极其强烈的表现。此外费正清的高足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开始着手清代制度史的研究,并以《清代官僚体系的内在组织》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广泛涉猎《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处分则例》等史料,最终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清代官僚体系的内在组织》一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即“法律的、规范的与沟通的视角”,充分表明他需要通过法律的视角考察清代官僚体系的组织与运作,无不体现出该书所具有的法律研究色彩,可以说是清代行政法律研究的经典之作。
费正清这样的学术意识不仅对美国汉学研究影响深远,而且也为美国法学界所高度关注。哈佛大学法学院与费正清创建的东亚研究中心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合作,于1965年发起成立了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专门对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法律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由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出任首届主任。孔杰荣不仅是个出色的学术研究组织者,也是一个中国法律研究的多产作家,是美国这一时期中国法律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于1968年公开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司法:1949-1963》,随后又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法律研究的学术进展加以归纳和总结,于1970年编写了《当代中国法》一书。然后他又与台湾学者、国际法学权威丘宏达合作撰写了两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法》,并与人一起合编了《中国传统法律论文集》,其中多是西方汉学家有关中国法律传统的专题文章。与孔杰荣同时着手中国法律研究的先驱人物还有包恒(David C. Buxbaum),他是尼克松访华后第一位应邀到访中国的美国律师,并在中国广州等地开办律师业务,后来还扩展到中国台湾、香港以及蒙古、日本、韩国等地,在中国、蒙古长期居住达三十余年。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发表有关中国刑法、婚姻家庭法以及商业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方面的专业论文,著述颇丰,尤其是在国际私法领域,影响深远。他以一己之力主编了《历史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婚姻家庭法与社会变革》一书,对中国的婚姻家庭法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和比较研究。不仅如此,他也一直是玛丁戴尔-哈伯(Martindale-Hubbell)出版的《中国法律摘要》和《蒙古法律摘要》的主要撰稿人及修订者,被公认为国际私法和中国法律领域的专家。
继孔杰荣之后担任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也是中国法律研究的一道丰碑,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并且注重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联系起来,其《窃书为雅罪:中国文明中的知识产权法》一书可谓是典型代表。除了孔杰荣与安守廉两位旗帜人物,这一时期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代表人物还有布迪(Derke Bodde,又译为卜德)、马伯良(Brian E. Mcknight)、皮文睿(R. P. Peerenboom,又译为裴文睿)、钟威廉(William C. Jones,又音译为威廉·琼斯)、庄为斯(Wallace Johnson)、桂思卓(Sarah A. Queen)等。布迪早在1963年就在《美国哲学学会会刊》上发表过《中国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后来又以该文为基础,与法学家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作,运用英美案例分析的方法,从清代案例汇编《刑案汇览》中精选出190例加以分析和评议,审视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及其思想观念,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马伯良著述颇丰,主要致力于宋代的法律问题研究,早期所著《中国南宋的乡村与官僚》开始触及到中国古代基层管理的一些法律问题,其《宋代的法律与秩序》一书则对宋代的法律实施与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揭示出了宋代法律实施与刑事政策的一般模式及其变迁方式。他还著有《仁慈的品质》,其中对中国古代的刑事司法问题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析。他还独自翻译了宋慈的《洗冤集录》,并与人合作翻译了《名公书判清明集》,并加以注解和评介。此外,他的《传统东亚的法律与国家》一书也有对中国法律方面的相关论述。皮文睿早年专注于中国古代的自然法问题,对儒家、道家的自然法思想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其《古代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一书专门就马王堆所发现的《黄老帛书》进行研究,对中国古代的自然法观念给予了非常独到而精彩的阐释。钟威廉是清律与新中国民法的研究专家,主持翻译了《大清律例》,译介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大量民事案例,也有系列中国法研究的论著问世。庄为斯则于1979年和1997年分两卷将《唐律疏议》先后译出予以出版,并就唐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发表过相关论文。桂思卓在对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重点阐释了董仲舒对秦律的改造以及为汉代法律所提供的理论指引,从而重塑了帝国时期的礼法传统。此外,高道蕴(Karen Turner)、宋格文(Hugh T. Scogin, Jr.)、蓝德彰(John D. Langlois, Jr.)、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爱德华(R. Randle Edwards)、欧中坦(Jonathan K. Ocko)、郭锦(Laura A.Skosey)、孔纳(Alison Wayne Conner)、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等人都是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中国法律研究专家,都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面世。其中高道蕴与中国学者高鸿钧、贺卫方合编了《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一书,收录了11位美国汉学家有关早期中国法律性质、唐宋时期法典编纂与解释、清律三个方面的12篇论文,稍后他又与美国两位学者合作编辑了《中国法治的限度》一书,除了自己撰写导论之外,共收录了包括安守廉、欧中坦等在内的12位西方学者论述中国法律传统以及现代法治的相关论文,影响颇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致力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华裔汉学家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在20世纪末转而研究中国法律史,于1996年推出了《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开始对美国汉学的中国法律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引领了21世纪美国汉学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格局。
相比于美国汉学的繁荣局面及其研究风格的变化,欧洲汉学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律研究仍然保留了传统汉学的基本特点,几乎还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内容来加以对待,其主要研究领域大多还是指向中国古代社会,因此研究方法上也主要依托传统汉学的文献分析,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只是略有侧重,作为传统汉学中心的德国与法国更是如此。德国完整保留了传统汉学的研究风格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传统的关注,譬如宾格尔就先后在汉学刊物Studia Serica第9卷第2分册以及Oriens Extremus杂志第19卷第1-2期合刊号上分别发表了《传统中国法有关精神病人与过失犯罪的惩罚》《马克斯·韦伯有关帝制中国的法律与司法的一些看法》两篇论文,还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习惯法方面的专题文章。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则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于1960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专著,同时还在德国的《比较法杂志》第56期上发表了有关明代土地税问题的论文。傅海波(Herbert Franke)作为辽金蒙元史的研究专家,法学与汉学双修,对辽金蒙元的法律研究颇有成就。此外兴趣广泛的汉学家奥斯卡·威格尔(Oskar Weggel)也对中国的法律问题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著有《中国法律史》一书。
法国由于社会学和历史学占据优势,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兴趣日益萎缩,很少出现有关中国法律研究的专门著述,但是白乐日(Étienne Balazs)可能是个例外。他本来出生于匈牙利,求学于德国,后来前往法国并得到马伯乐的指导,二战后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从事汉学研究,随后又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早在1954年,白乐日就翻译出版了《隋书·刑法志》,他还先后发表过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官僚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城市行政与司法制度等方面的论文或著作,死后很多内容被人精心加以编排出版了一些论文集。另外他还有很多去世时尚未发表或没有完成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就有中国法律史与法律人类学文献方面的研究和没有完成翻译的《晋书·刑法志》。他还在生前为了授课的需要,专门搜集和整理了有关汪辉祖的文献资料,对其《学治臆说》进行了部分翻译和评论。此外,谢和耐因为注重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会涉及到古代中国的一些法律问题,他在佛罗伦萨1978年出版的《中国法律》上所发表的《论古代中国法律中的责任观》,具有较好的学术意义。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由于擅长有关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著述牵涉到一定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法律思想与法律观念方面,如《法家的形成》以及两卷本的《王道:有关古代中国治理体制精神之研究》。到了20世纪末期,巩涛(Jérôme Bourgon)开始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汉学明星,他在1994年以题为《沈家本(1840-1913)与帝制晚期的中国法》的学位论文获得历史与文明专业的博士学位,为后来成为欧洲汉学界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因此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汉学研究,真正将中国法律问题作为独立的学科内容加以研究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当首推荷兰,何四维(A. F. P. Hulsewé)对秦汉法律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汉学研究的典范。但何四维本来是德国人,是因战争原因移民到荷兰的,所以受到德国汉学的影响还是不言而喻的。而作为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并长期担任职业外交官的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一生不仅致力于翻译和创作《武则天四大奇案》《狄仁杰奇案》而最终汇集为百万字文学巨著《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用文学语言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法律故事,而且还译有中国法医学著作《棠阴比事》,同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比较长的绪论,对帝制中国的有关法律问题特别是县级机构的司法程序进行了精彩介绍和描述。同样曾为外交官的梅耶(Marinus Johan Meijer)在出版《中国近代刑法导论》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先后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法律的专著以及一系列论文。其对中国法律的研究不仅相当专业,而且研究领域广泛,成果斐然。此外,伊德维(Wilt Idema)与许理和(Erik Zürcher)为了隆重祝贺何四维八十华诞,联合编纂的《中国秦汉的思想和法律:献给何四维教授八十岁生日的研究文集》也收集了许多作者有关秦汉法律的文章,颇为引人注目。
英国虽是欧洲国家,但因其与美国的特殊联系,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相比于欧洲大陆国家而言,完全可以用繁荣昌盛加以形容。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又译为杜希德)作为该时期英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不仅受到传统汉学的熏陶,而且还曾在日本师从著名的中国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使得其汉学研究和教学高度关注法律以及其他制度层面的东西,这对英国汉学日渐注重中国法律研究,并使之不断走向专业化和独立性影响甚巨。崔瑞德在自己与费正清担任总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丛书中就注重法律制度方面的内容,譬如邀请何四维为秦汉史卷专门撰写秦汉法律部分。他不仅在自己的一般中国史著作中注意挖掘法律制度层面的材料及其解释,而且其实也是唐代法律研究的专家,并且在《威尼斯文明研究》与《泰东》刊物上先后发表过两篇有关唐代法律的专业论文。除了崔瑞德,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他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历史梳理上。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十八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和西方的人间法律和自然法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和展开,其所提出的“自然法”与“自然法则”的划分甚至对西方法理学特别是自然法理论的历史发展都颇有影响。此外,鲁惟一(Michael Loewe)也有一些论著涉及到中国法律制度问题,特别是其《汉代行政记录》一书在研究居延汉简的基础上,对汉代的行政制度尤其是军事兵役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正是在崔瑞德与李约瑟的领导和推动下,英国汉学在20世纪下半叶获得了迅猛发展,也对中国法律尤其是古代社会的法律传统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没有美国那么多汉学家投入中国法律专题研究,但还是有着一些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斯普林克尔(Sybille van der Sprenkel)可能是该时期中国法律研究最早的开拓者,她以自己的社会学专长对清代法制进行了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清代法制——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马若斐(Geoffrey MacCormack)是继斯普林克尔之后英国汉学家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扛鼎人物,公开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中国传统刑法》《传统中国法的精神》等专著,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最后应该指出,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留学、访学或旅居欧美的中国学者不仅汉学造诣自是不在话下,而且专攻法律或涉猎中国古代制度,他们在欧美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法律的论著为很多西方汉学家所倚重,这对20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法律研究颇有影响,其中吴经熊、瞿同祖、萧公权、杨联陞等人都属于杰出代表。吴经熊曾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并与当时国际一流的法学家如霍姆斯、卡多佐、庞德等人都有学术交往,他的很多著述都为西方汉学家所关注。瞿同祖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期间加入了“中国史研究计划”,他在中国初步完成、后来又在国外补充、修改并译成英文在法国出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对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可以说是置于案头的必备参考书目。他的《汉代社会结构》也为西方汉学家相当推崇,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还曾为该书亲自作序。萧公权在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和康奈尔大学哲学系,主要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中国宪政问题颇多阐释,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对西方汉学影响颇深。杨联陞曾为哈佛大学燕京讲座教授,与海内外学人广有交往,对中国经济史与制度史的研究闻名于学界,其学术精华多收录于《中国制度史》一书,对西方汉学的中国法律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亦是不言而喻的。
三、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全面渗入时代的中国法律研究
人类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两大阵营对立的时代彻底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欧洲联盟、俄罗斯、印度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加上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全球化的发展格局日趋复杂多变。基于这样的背景,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全方位的推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关注也日显迫切,汉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科学全面渗入西方汉学,特别是对中国政治与法律的运作问题,开始成为西方汉学或海外中国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继续扛起汉学研究领袖的旗帜,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法律领域,还是在现代中国的法律实际运作方面,都有数量众多的研究专家。除了哈佛大学等老牌的汉学研究重镇,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也纷纷投身于中国研究。孔杰荣作为中国法律研究的先驱人物,也从哈佛法学院以及东亚研究中心转而受聘于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并于2005年创建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并担任首届主任,使其成为美国中国法研究的又一个学术重镇。在这样良好的研究氛围和有利条件下,早已声名鹊起的汉学家继续开脱新的研究领域,并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带动了一大批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形成了一个璀璨夺目的研究队伍。
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原本致力于中国尤其是明清以来经济史、社会史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经济史研究的华裔汉学家黄宗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以来,日益认识到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是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通道和纽带,因此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加快了研究的步伐。除了翻译出版了原先的《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外,接着又以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与《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两书,完成了他所谓的中国民事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他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高度注重挖掘诉讼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从中可以发现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从而呈现出法律实际运作的实践历史。除了民事法律实践历史研究的系列著作之外,他还与尤陈俊联合主编了《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研究范围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内容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除此而外,黄宗智还在《中外法学》《政法论坛》《中国法律》《清华法学》等法学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有关中国法律的学术论文。不仅如此,黄宗智还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与美国同行孔杰荣、安守廉、爱德华、鲁布曼(Stanley Lubman)、麦柯丽、马克·艾力(Mark A. Allee)、宋格文、毕仰高(Lucien Bianco)进行学习交流,同时他的妻子白凯(Kathryn Bernhardt)以及学生白德瑞(Bradly W. Reed)、苏成捷(Mathew Sommer)、胡宗绮(Jennifer M. Neighbors)等深受其学术影响而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白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跟黄宗智合编过《中国清代与民国时期的民法》一书,并出版独著《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随黄宗智来到中国后,她又将《中国的妇女与财产》一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白德瑞则于2000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推出了《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主要利用巴县档案考察了帝国衙门中书吏与差役所组成的权力网络及其运作方式,揭示了帝国行政与司法的微妙机制,进而触碰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其研究手法无疑贯彻了黄宗智实践历史的学术进路,特别是黄宗智有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分,堪称实践社会科学甚至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典范。苏成捷更侧重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一种实践历史或经验研究,其所著《帝制中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一书,充分利用诉讼档案,以一种实证研究的方式力图解释晚期帝制中国的性立法,特别是清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司法实践。他后来出版的《中国清代的一妻多夫与妻子贩卖: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一书继续推进了这一研究风格,但写作水平相比于《帝制中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而言,似乎略欠火候。胡宗绮(Jennifer M. Neighbors)则对法律本身的问题更为关注,其《意欲何为:清代以来刑事法律中的意图谱系》一书以犯罪意图为核心,由低到高探讨了中国帝制时期杀人罪的谱系以及近现代犯罪意图的演变,更具有浓郁的法学专业色彩。
这一时期的美国汉学除了20世纪下半叶就已非常活跃的汉学家,譬如马伯良、宋格文、麦柯丽等等,还涌现出了很多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新锐人物。作为美国“新法制史”学派代表之一的步德茂(Thomas M. Buoye)围绕清代刑事法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一书,研究功力相当深厚。犹他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戴真兰(Janet M. Theiss)受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女性法学影响,也十分关注清代女性、家庭、财产等问题,公开发表了《18世纪刑事案件中配偶暴力的叙事及对男性气概的批判》《18世纪中国的女性自杀、主观因素与国家》以及《清代精英参与司法制度及其对法律实践和法律原则的影响》等数篇论文,并出版了专著《丑事:中国18世纪的贞节政治》。埃默里大学的法学教授络德睦(Teemu Ruskola)强调从多元视角出发研究法律的历史与理论,尤其注重以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优势的切点,从比较的和国际的角度对中西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实践进行分析和反思,其成名作《法律东方主义》通过聚焦中国与美国,剖析东方主义意识对中国法与美国法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与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法律东方主义成为一个经典话题。
受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这一时期即使比较传统的汉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包括华裔汉学家也对中国法律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合了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各自的研究优势,出现了很多颇值一提的作品。专门致力于早期帝制中国研究的陈力强(Charles Sanft)不仅在自己的两部历史著作中对秦汉法律尤其是法律与传播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法律史论文。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中专门探讨了从先秦到秦汉的法律发展问题,并从法律与宗教、法律与行政、法律与语言、法律与惩罚、法律与侦查、法律与劳役等角度对秦汉法律进行全方位的介绍。曾小萍(Madeleine Zelin)从早期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日益转向法律史领域,特别关注法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以及中国近代早期法律、文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她的最新著作《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是对18世纪至20世纪初四川南部先进工业社区的研究,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发展中习惯法律和商业惯例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见解。她还与欧中坦、加德拉(Robert Gardella)合作编写了《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一书,收集了11位作者不同角度的论文,对中国近代的契约、产权与商业实践所涉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马礼彬(Mark P. McNicholas)专门利用刑事档案研究帝制中国特别是帝制晚期普通民众与国家之间的遭遇和冲突,尤其是犯罪、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清代冒充捕役问题研究》一文就是难得的力作。贾空(Quinn Javers)则利用四川等地的相关档案,专注于清代特别是四川地区的暴力、法律、地方社区和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谎言的逻辑:晚清四川地区的诬告现象及其法律文化》与《晚清四川地区的冲突、社区与犯罪》等学术论文,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专著《晚清四川地区的冲突、社区与国家:实现地方正义》,考察了晚清时期四川地区350多起法律案件,特别关注其中所涉及到各类死亡案件,通过挖掘暴力和冲突的社会根源揭示出了帝制晚期社区与国家所发挥的基本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展示了日常暴力在秩序、规训和社区建设中所具有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关于晚清权力、法律、正义和国家角色的理论视角。戴史翠(Maura Dykstra)是明清史的研究专家,对晚期帝国制度史、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史以及官僚主义与知识史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专注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其对日常政治和社会互动的影响,发表了一些有关清末新政的专业论文,其专著《日常帝国:十八世纪清朝的意外行政革命》是一部视角相当独特的清代制度史研究力作。克礼(Macabe Keliher)作为一名对清代以及现代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兴趣的历史学者,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蒙元法律、大清会典方面的学术论文,其专著《礼部与清中国的形成》考察了清代如何在明代礼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对理解中国古代的礼法传统具有相当大的学术意义。
华裔汉学家除黄宗智外,还有几位学者在这一时期也相当活跃,同样注重引入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研究中国法律传统。张泰苏先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和数学学士学位、法律博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这种得天独厚的学术背景使得其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得心应手而游刃有余,特别擅长中西法律史的比较研究,其代表性著作《儒家法律和经济学:前工业革命时期中英的亲属与财产关系》从儒家思想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和英国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并比较和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异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好评如潮,热议不断。陈利则为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出身,后来转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及法学院任教,特别注重从中西关系以及中西文化界限的角度认识和研究中国法律传统,其代表作《帝国视野中的中国法》一书以“西方知识的形成与转变”为主题,探讨了西方世界在鸦片战争前后对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看法,并进而阐释了该时期的中西交往对18、19世纪的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如何导致欧洲关于现代法律与现代政府的各种争论之产生,从而为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政治实践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美国汉学这种多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趋势在21世纪获得了深入的发展,甚至使得过去专注于人文科学的传统汉学研究也不甘寂寞,一些汉学家开始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法律领域,别有心裁地开辟了中国法律研究的新天地,其中深耕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尤其是致力于明清小说研究的何谷理(Robert E. Hegel)可谓是典型代表。何谷理将英美比较流行的“法律与文学”这一研究范式引入到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领域,先是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后来为了考察明清时期的成文法和法律写作以理解法律在传统中国社会想象中的地位,专门策划和召开了一场有关明清小说与法律的专题会议,并将会上所收论文以书名《帝制中国晚期的写作与法律:犯罪、冲突与审判》结集出版,将法律、历史与文学联系了起来,阐明了作为文化实践的写作与司法行政之间的复杂交汇之处。此后不久,何谷理又继续利用北京市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刑科题本”等清代司法档案,精心选译了20个经典案例,编成《中国18世纪的真实犯罪:二十案史》一书,用文学叙事的手法讲述这些案例故事的来龙去脉,揭示清代社会关系与法律程序的实际样貌,也非常值得一读。
于此可见,美国汉学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以及交叉学科的穿梭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普遍倾向。欧洲尽管也开始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但还是更多保留了传统汉学的研究特点,注重文献分析仍是其中国研究的看家本领。德国以陶安(Arnd Helmut Hafner)、劳武利(Ulrich Lau)、史达(Thies Staack)为代表的汉学家,继续发挥传统汉学的研究特长,在简牍研究尤其是秦汉法制史领域颇有造诣。他们三人先后都曾参与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具体研究工作,发表过相关论文并有专著出版。陶安不仅以德文、英文、日文发表了相关论文或出版了相关著作,如用日文出版的专著《秦汉刑罚体系的研究》,还直接用中文在中国大陆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其中以《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释文释注》最具有代表性。劳武利先与吕德凯(Michael Lüdke)对张家山汉简中的《奏谳书》进行了译注研究,成为张家山汉简法律文献的第一部西方汉学专著,后来又与史达合作撰写了《中华帝国形成阶段的法律实践》一书,在对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刑事案例进行译注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秦汉时期法律实践的相关问题。德国同时也有一些专注于当代中国法律研究的汉学家,只是为数不多,何意志(Robert Heuser)可谓是典型代表。他早在1999年出版了《法治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导论》一书,其中尽管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但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要素以说明当今中国法律的形成过程,该书的主要篇幅还是致力于介绍当今中国法律的渊源、法律职业以及主要法律部门的结构体系。此后,他还先后出版了《中国环境保护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中国行政法》《入WTO后中国外商投资法》《中国经济法概要》等一系列著作。此外荷兰的汉学家也跟德国一样,传统汉学的研究特点仍然比较浓烈,但也有一些汉学家开始受到社会科学的洗礼,强烈关注中国的社会实际问题,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运用文化史的角度与方法研究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司法运作问题,堪称“小题大做”的典范,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法国因为一直是社会学的思想摇篮,相比于德国的汉学研究而言,受社会学影响较深,这一时期中国法律研究的核心人物巩涛(Jérôme Bourgon)便是代表。巩涛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里昂东亚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曾以法文或英文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法律史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些文章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学术刊物上刊出,目前经过中国数位学者的组织和翻译,收录了其11篇论文拟在中国大陆结集出版。除了巩涛,法国还有一批成长迅速的中青年汉学家,他们的中国法律问题研究也颇有特色。非常年轻的康斯坦(Frédéric Constant,又名梅凌寒)曾在中国进行长达五年的学习和研究,主要研究蒙古法和清代的法律多元化问题,已经公开发表了二十余篇有关元明清时期的学术论文,其中部分论文开始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刊发,学术前途未可限量。施振高(Claude Chevaleyre)致力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强迫劳动、奴役和贩卖人口的历史研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对中国近代早期的法律史以及法律档案也了如指掌,其长篇博士论文专门着眼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奴婢身份与地位研究,比较深入触及到了中国身份法史的一些重要问题。
英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出的汉学研究者不多,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康佩理(Ernest Caldwell)倒是有些夺人耳目。他既对中国包括台湾地区近现代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宪政与人权问题颇有研究的兴趣,也对古代中国特别是早期帝制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深入探讨,撰有专著《成文中国法:睡虎地秦简所见法律的形式与功能》,以睡虎地秦简以及其他出土简牍、传世文献为材料,分析和研究秦代法律的文本及其功能。相比于英国,加拿大这一时期在中国法律方面的研究要更为发达。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叶山(Robin D. S. Yates)一直倾心于古典中国研究,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关注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文献,先后发表过相关论文,进入21世纪后更是持续发力,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中国早期历史教授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合作翻译了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并在译注的基础上写成两卷本的《早期帝制中国的法律、国家与社会——张家山247号墓所见法律文本的评述与译注研究》,堪称汉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与历史系教授、《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Timothy Brook)近年来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问题甚至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产生了研究兴趣,与法国的巩涛以及加拿大的格力高利·布鲁(Gregory Blue)合作撰写了《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很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彭德(Pitman B. Potter)对当代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他早年在美国求学,曾于2005-2007年先后三次来华访问,并与顾肖荣合编了《“选择性适用”的假设与中国的法治实践》一书,所汇集的一系列文章探究了与贸易和社会福祉有关的国际法标准在中国的适用。他除了关注中国国际贸易方面的相关法律问题之外,还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过系列论文,成为他晚年学术研究的焦点。
四、结语:中国法律研究的汉学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汉学家不仅成长、生活于西方世界,深谙西方学理,而且他们大多都精通汉语,比较全面而深入阅读过有关中国文明的经典文献与研究资料,甚至还在中国进行过一定时间的访问或考察,因此他们对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既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学者,也有异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这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文明语境上的隔膜,从而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借助另一个世界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还可以再从这种眼光出发,凭借我们的文明视角去检讨西方世界.“这种双重审视和检讨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不同文明语境的认知,从而对不同的法律传统进行卓有成效的比较、鉴别和判断,拓宽我们认识法律属性的文明视野与学理路径”,这无论是对中国学界来说,还是对西方汉学甚至整个西方学界而言,都能增进交流,深化认识和理解。西方汉学也正是在这种双重交流的背景下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现代西方汉学日渐关注中国法律问题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日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研究阵营与研究人员来看,西欧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属于中国法律研究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法国与德国几乎代表了当时西方汉学家中国法律研究的最高水准,荷兰与英国也紧随其后而扶摇直上。然而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的中国法律研究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基本格局,同时华裔学者与社会科学学者特别是法学学者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强,反映出西学与汉学、汉学与法学研究之间的双向互动,从而使得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其次,从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汉学对中国法律问题的研究,深受传统汉学的影响,主要致力于古代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特别着眼于一些法律文献的梳理、翻译和解读。但是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美国汉学倡导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联系起来,西方汉学家已经不再局限于古代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对近现代中国的法律问题都有了相当浓厚的研究兴趣。最后,从研究方式与研究方法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汉学仍然以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研究方法作为中国法律研究的基本范式,但是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美国汉学所倡导的社会科学以及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日渐成为中国法律研究的主流取向,这在21世纪以来可以说已经成为西方汉学中国法律研究的鲜明特点。因此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国学者对外交流与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汉学的中国法律研究必将得到深入推进,从而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来自异域的他者视角,促进中国法律研究及其实践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