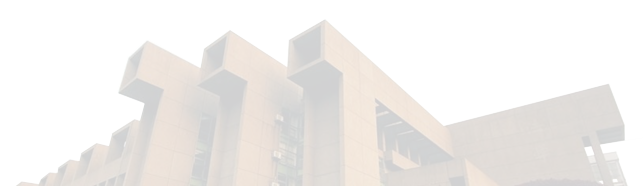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湖湘法学评论》2023年第1期“域外法学”栏目
作者】吉坦扎丽•甘古利(Geetanjali Ganguly),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博士研究生;乔安娜•赛泽(Joana Setzer),英国科学院博士后,任职于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维尔勒•海沃特(Veerle Heyvaert),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译者】马亮,法学博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讲师;连佑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区树添,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
【摘要】基于私人气候诉讼的历史和前景,该诉讼旨在要求私人主体承担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损害或损害威胁的法律责任。在消除诉讼资格、损害证明和因果关系等此类司法门槛的尝试失败后,新的私人气候诉讼的浪潮正在袭来,而这次绝不会注定失败。这是因为气候变化诉讼的科学、对话和法制背景正在迅速演进,法官可以借此重新审视对现行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的解释,以适应强化追究主要私人碳排放者法律责任的需要。此外,即便是未能胜诉的案件,也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法律和财务风险,从长远来看,能给应对气候变化案件的诉讼审理提供指导。
【关键词】私人气候诉讼;碳排放巨头;司法干预;气候变化因果关系;企业责任;气候风险披露
一 引言
在最近的演讲中,前美国宇航局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呼吁对拖延气候变化行动的政府和化石燃料公司提起一系列诉讼。汉森是气候科学的先驱,他认为针对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英国石油(BP)和壳牌(Shell)等公司对环境、当代及后代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是至关重要的行动。汉森目前正投入于一场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诉讼中,该诉讼由他的孙女和其他20个人提起。同样的,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也号召公民们“涌上法庭”,他们主张安全和清洁的环境权,追究主要污染者和疏忽大意的政府的责任并要求损害赔偿。
本文通过研究针对公司发起的气候诉讼的最新发展,试图为蓬勃发展的气候诉讼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认为,尽管上一波气候诉讼浪潮未能追究到私人行为者的责任,但第二波向法庭发起的诉讼浪潮并不一定会失败。第二波浪潮引起了较前一波更为广泛的讨论,并在迅速发展的科学、对话和法制背景下展开诉讼策略。我们认为,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为法官提供了新的机会,让他们重新考虑对现有法律和证据门槛的解释,以满足原告的举证责任,并以一种加强私营温室气体排放者问责的方式应用这些门槛。尽管迄今为止,对企业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的司法强制仍难以把握,但未来的发展情况会逐步改善。此外,即使是未能胜诉的案件,也有助于指导往后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裁决。
本文的结构如下:先是将研究放在更广泛的气候诉讼背景下,重点是解释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的显著特征;接下来扩展分析第一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的主要问题,探讨了重大案件中与管辖权、诉讼资格和因果关系有关的困境;接着讨论伴随当前诉讼的科学、对话和法制背景下的变化,以及它们对判决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再就是考虑第二波私人诉讼仍以失败告终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情况下气候诉讼的贡献(如果有的话);最后作出结论并提出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二 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
气候诉讼是一个宽泛的且处在发展当中的术语,它指的是一种迅速增长的新型诉讼,在这些诉讼中,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通常是法律论证和裁决的重要或关键的考虑因素。迄今为止,被认定为气候诉讼的案件已超过1000宗,仅在美国就有828宗,在其他25个国家中有263宗,其中大部分是自2000年以来提起的。大多数人将气候变化因素作为此类诉讼的次要成分。此类“附带气候诉讼案件”涵盖了如超出许可证许可范围作出虚假绿色广告以及能源或煤矿开采等争端。在美国以外的25个司法管辖区,超过四分之三的气候诉讼案件仅将气候变化视为法庭辩论的边缘性问题,仅承认气候变化因素具有相关性而非决定性。相比之下,战略性气候诉讼则是指为减轻、适应或补偿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而对政府(战略性公共气候诉讼)或企业(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施加自下而上的压力的案件。目前,战略性气候诉讼案件很少,但受到学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高度重视。
战略性公共气候诉讼的目标是通过取得禁制令来影响具有气候变化影响的公共政策或政策制定进程。对于政府未能解释的并与公共项目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案件,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公共监管行动(或不作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首先是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EPA)案(2007年),在该案中,美国环保局被裁定违反了《清洁空气法》规定的管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定义务。2015年的乌尔干达(Urgenda)案裁定,根据《荷兰民法典》第 6 章第162条的规定,由于未能采纳有足够雄心的减缓目标,荷兰政府违反了荷兰侵权法下对社会的注意义务该案开创了战略性公共气候诉讼的新时代。仅仅几个月后,在勒加里(Leghari)的一个鲜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裁决中,拉合尔高级法院(Lahore High Court)裁定,政府因推迟实施巴基斯坦的气候政策而违反了该国的人权义务。乌尔干达和勒加里等案例产生的势头促使从比利时到印度和美国的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法院都出现了类似的案件。
但是,本文的重点不是战略性公共气候诉讼,而是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它涉及的案例带有明确的目的,希望影响公司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行为和策略。21世纪初,北美法院审理了一小批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诉讼。受害者声称,这些公司的行为加剧了他们因极端天气事件而遭受的损失。这些案件因题材具有新颖性而备受瞩目,但都没有胜诉。原告发现要超越司法上的程序和实质性门槛极其困难。然而,这些令人沮丧的先例显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实际上,可以观察到,现在针对私人被告的第二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通常控诉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损害,并向主要的碳排放者寻求赔偿。
新一波将公司作为被告的努力有两个强烈的动机。第一个动机与它们的适宜性有关,换言之,企业是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的“适格”主体。可以说,能源、交通、农业和水泥等其他制造业企业的碳排放活动对气候变化负有集体法律责任。非政府组织和气候活动人士也声援了这一观点。例如,气候正义计划(Climate Justice Program)发布的一份报告写道:当今大气中三分之二的人为碳排放来自碳排放巨头。这些公司赚取了惊人的利润,却把产品的真正成本外包给了贫困人群,而贫困人群付出的代价则是自己的住房、种粮能力,甚至是生命。
此外,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和提高韧性的努力中,企业被视为越发关键的角色。由于发电和运输消耗的燃料产品在全球产生了近70%的温室气体,企业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考虑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企业应该参与基础设施提供、开发和土地使用。
第二个动机与私人气候诉讼的潜在效果有关。如果能成功地针对排放量占比很大的那一小部分公司采取行动,将能产生相当大的全球性影响。理查德•希德(Richard Heede)的工作成果同样支持了这一论点,其研究旨在衡量“碳巨头”(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者)对碳排放的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徐(Hus)认为,“追究那些温室气体排放者的直接民事责任”是唯一有望成为“灵丹妙药”的诉讼策略。徐进一步指出,“(民事)诉讼策略本身是一种潜在的监管手段,因为追究责任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让温室气体排放者争相避开不受欢迎的聚光灯”。因此,针对碳巨头的私人气候诉讼可能比公共诉讼或替代治理策略更有效。
此外,转向以公司为目标的私人诉讼,其目的与气候变化治理的跨国化是一致的,都是为应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主持下的各国不充分的国际监管。由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附件一成员国与非附件一成员国之间的区分被取消,以及对国家承担损失和损害责任的想法的强烈抵制,促使人们开始呼吁采取一种新的方法,重点关注非国家行为者的责任,特别是在附件一和非附件一国家内均有运营且接受跨国监管的碳排放巨头。
三 第一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
第一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发生在 2005 年至 2015 年,主要集中在美国。在州地方法院提起的几起诉讼都因政治问题的不可审理性而被驳回。最显著的例子是科莫诉墨菲石油公司(Comer v. Murphy Oil)和基瓦丽娜诉埃克森美孚公司(Kivalina v. ExxonMobil)。在这两起案件中,原告均认为被告(能源生产商)从事的排放活动极大地加剧了气候变化,因此,被告对他们遭受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伤害负有责任。在科莫案中,原告(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声称被告能源公司的排放活动加剧了气候变化,并增强了卡特里娜飓风的破坏能力。同样,在基瓦丽娜案中,原告(来自阿拉斯加的伊努伊特人)声称,一批包括埃克森美孚在内的能源公司的活动对温室气体的跨境排放负有责任,这对基瓦利纳的气候造成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海岸侵蚀、北极海冰和永久冻土的融化。这些影响威胁到他们村庄的存续和他们的生存方式,最终导致他们被迫迁移,流离失所。
在第一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中,常见的指控都是围绕着企业应当弥补因其碳排放行为造成的法益损害这一论点展开的。因此,大多数案件都围绕着诉讼资格和管辖权等程序性问题以及因果关系和损害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下文各节以科莫案和基瓦丽娜案为例来进一步探讨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审理。
(一)起诉资格和管辖权
在第一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中,被告以程序为由提出动议并成功地使法院驳回原告主张。在美国,被告通过援引诉讼资格和政治问题策略作为第一道防线来挑战法院的管辖权,成功阻止了几起气候变化诉讼进入审理阶段。根据美国宪法第3条常设原则规定,联邦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以下情况:(1)原告实际上遭受了损失;(2)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追溯到被告的不当行为(因果关系);(3)能够由法院纠正。除非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否则原告将失去诉讼资格。因此,关于诉讼资格的规定给原告试图提起对气候变化造成损害的诉讼设置了相当大的困难。
尽管法院接受了原告主张的损害(例如,因海平面上升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因景观变化造成娱乐或美学价值的损失),但法院通常拒绝接受关于因果关系和可补救性的主张。在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中,法院裁定,原告马萨诸塞州作为一个州,有权获得“特殊关怀”(specialsolicitude),并认为未能监管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会对州造成“实际的和迫在眉睫的风险”。相反,私人原告并不能从“特殊关怀”中受益。因此,联邦法院在该案后的裁决中都否认了私人原告在气候变化方面起诉监管机构或温室气体排放者以寻求救济的诉讼资格。
另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私人诉求也遭遇了政治问题排除原则的阻碍,这一原则规定联邦法院不审理某些争议,因为这些争议应由政府政治部门解决。根据美国宪法,政治问题排除原则规定法院只能对被认为是可审判的法律问题进行裁决。因此,法院通常避免裁决具有内在政治性的问题。在马萨诸塞州诉联邦环保署案和美国电力公司(American Electrical Power)诉康涅狄格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美国环保局独享根据《清洁空气法》规范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力因此,美国法院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实问题交至行政部门,并认为此类问题需要初步的政策性审查。
在科莫案和基瓦丽娜案中,原告提起了一系列侵权索赔,涉及妨害、民事共同侵权行为(civil conspiracy)和过失。被告公司成功地回应道,原告主张的论点本质上是不可裁决的政治问题,法院不具有管辖权。被告认为这类问题更适合由政府部门来解决。在这两起案件中,地方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裁定根据政治问题排除原则,原告的妨害赔偿请求不能被考虑。因此,两个法院都裁定原告人没有诉讼资格。
科莫诉墨菲石油公司案中的原告上诉成功后,气候诉讼案的发展似乎出现了更有利于私人原告的转折。地方法院的专家组裁决原告有诉讼资格,其诉求是可被审理的。然而,此案最终被驳回,向美国最高法院的申诉也被驳回。2011年,同一原告试图向密西西比州南部地区法院提起新的诉讼,但法院根据既判力原则、诉讼时效、政治问题等原由驳回了原告,认为原告既没有诉讼资格也无法证明因果关系。
(二)因果关系
证明因果关系(行为者的行为与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之间的联系)的困难也是私人气候诉讼的阻碍之一。因果关系要求原告证明损害和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满足责任者应承担损害赔偿的举证要求。但是,即便损害由气候变化造成是能被证明的,在事实上和概念上确定造成损害的行为者也存在较大困难。基瓦丽娜诉埃克森美孚公司案也同样说明了原告很难令人信服地指出气候变化造成危害的原因。地方法院认为,原告既不能证明埃克森美孚的活动对造成的损害有“重大可能性”,也不能证明其损害根源可追溯到被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而言,法院的结论是原告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因为“要在任何特定时间追踪到特定的人或实体的排放量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是不现实的”。第九巡回法庭确认了地区法院的裁决,尽管它并没有重新考虑政治问题排除原则和诉讼资格引发的问题。相反,第九巡回法庭认为联邦立法优先于原告主张的联邦普通法,并解释说,解决全球变暖影响的任何方案“都必须掌握在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手里,而不是联邦普通法手里”。在科莫诉墨菲石油公司案中,地方法院同样也裁定原告不能证明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四 第二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
尽管目前私人气候诉讼还没有胜诉的先例,但私人气候诉讼在未来并不一定就会失败。迅速发展的科学、对话和法制背景为第二波战略性私人诉讼浪潮扫清了道路,使案件有更多机会克服曾阻碍早期尝试的诉讼资格、损害和因果关系等司法障碍。新一波私人气候诉讼受到2013年“碳排放巨头”研究报告(Carbon Majors study)的推动,并已扩展到美国以外的新的司法管辖区。这股浪潮在2015年势头强劲,台风幸存者、倡导者,包括东南亚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Southeast Asia)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线上支持者向菲律宾人权委员会提交了请愿书。紧随这一举措,柳亚诉德国莱茵集团 (Lliuya v. RWE)等案也于 2015 年提起;2017年,加州两个县(San Mateo and Marin County)和帝国海滩市(city of Imperial Beach)提起的诉讼涉及37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及贸易集团;盖伊•亚伯拉罕斯诉澳大利亚联邦银行(Guy Abrahams v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一案,于2017年再次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纽约市于2018年1月对全球5个最大的碳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壳牌(Shell)、英国石油(BP)、雪佛龙(Chevron)和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提起诉讼。在撰写本文时,第二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尚未达至顶峰,因为关于新诉讼和计划提起的诉讼的新闻仍在继续定期报道。
着眼于科学背景,我们研究了气候科学的新发展是如何提供新证据,以加强气候变化引发的损害与公司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这有助于清除获得诉讼资格和维护主张时遇到的主要障碍。关于法律对话,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气候变化危害与分散的企业被告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就能有更好的前景,转而提高烟草和石棉诉讼胜诉的先例价值。我们还回顾了近期讨论中关于董事责任和披露要求的变化,这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什么是负责任的“气候变化行为”的理解,拓展了新的索赔人类型。最后,我们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环境法制背景,并确定在哪些司法管辖区提起基于气候的诉求可能会在庭前举办更具可行性的听证会,从而增加私人气候诉讼成功的可能性。
(一)科学背景
推动新一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以及增加法院支持向大量排放者索赔的可能性的首要因素,正是诉讼演变的科学背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天的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与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包括:(1)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科学知识得到发展和巩固,不断更新更为全面的本地化数据;(2)量化世界最大碳巨头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比例越发具有可能性;(3)归因科学的发展。
1.气候科学的适用性不断增强
第一波战略性气候诉讼的基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气候变化综合数据。在美国,科莫诉墨菲石油公司(Comer v. Murphy Oil)一案为各州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科学来证明人为气候变化的存在开了绿灯。原告的起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证的科学,并提供了预测全球气温上升的气候模型作为支持证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数据被视为足以满足“公平可追溯性”(fair traceability)的要求。尽管该案最终被发回地方法院重审后还是败诉了,但上诉法院对气候变化因果关系问题的介入超出了表面驳回的范围,这暗示了司法在将来有可能认可一个较宽松的气候变化因果关系阈值。
新一波的战略性气候诉讼浪潮利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指出的“在人为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强有力的科学共识”。在公共气候诉讼领域,荷兰的乌尔干达案恰当地表明,民法管辖区的法院愿意接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将其视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气候变化是一种严重的人道主义和地球威胁的证据。
此外,原告正在更有策略地使用气候科学,在诉讼中加入了最新和当地的科学证据。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到加利福尼亚帝国海滩,美国地方当局最近发起了一系列诉讼,声称雪佛龙和荷兰皇家壳牌等大型公司对于因消耗化石燃料产品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即使在未来没有任何排放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海平面上升)负有很大的直接责任。因此,要求他们赔偿应对洪灾事件以及当前和未来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气候变化损害的费用。论证中,原告依靠的就是最新的海平面上升科学知识和脆弱性评估。这些案例将重点从气象变化转移到了海平面变化,而海平面变化明显与全球变暖有关。绘制更高精度的易被淹没区或因海平面上升导致更大洪灾风险的区域地图,可能有助于改善以前难以将气候变化损害可视化或予以确认的困难局面。
2.量化企业的历史排放量
第一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中的被告企业通常认为,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于历史或全球排放量而言微不足道,因此,不能说他们直接造成了气候变化危害或对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人为气候变化的时间跨越数十年,地理范围跨越各个大洲。温室气体排放的扩散性和跨界性使得很难将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因于特定行为者。法院不愿对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作出确切结论,并且倾向于将气候变化视为集体政策而非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通常将气候变化难题视为不适合司法审查或裁决的政治问题。
但是,气候科学的进步能帮助研究人员识别出潜在的被告群体,他们对气候危机的“贡献”是可识别的、可测量的和显著的。2013 年,理查德•希德(Richard Heede)首次量化并绘制出了1854年至2010年期间最大的9家碳排放者的累积排放量。该研究计算出这些“碳巨头实体”的排放量占全球人为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这项研究及其方法也有争议,但希德的研究结果经同行评审后发表在了学术期刊《气候变化》(Climatic Change)上。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这90个碳巨头在1988年以后的碳排放量占其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这表明问题的根源比之前设想的更接近,也更容易追溯。
许多人认为这项研究是“关于气候变化责任分配争议的转折点”,并称赞其率先在气候诉讼中识别出一类“分散在各地的被告”,这能帮助原告主张气候变化损害赔偿的诉求。全球环境法联盟(ELAW)声称,此类研究的出现“消除了以前要求基层律师在追究主要碳排放者责任时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将“帮助到世界各地的为了让公司承担责任的律师”。
确实,碳巨头研究发表后不久,就成为两起前所未有的私人气候变化诉讼的理论基础。第一起是菲律宾重建运动(Philippines Reconstruction Movement)和绿色和平东南亚组织于2015年9月向菲律宾人权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该请愿书要求委员会行使其调查权力,调查碳巨头企业在引起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中的影响。此案的核心法律问题是:“是否追究这些碳巨头企业……因其造成的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而可能对人权产生影响的责任。”碳巨头研究是帮助塑造绿色和平运动的“科学研究基石”之一。
第二起是来自秘鲁安第斯地区的农民索尔•卢西亚诺•柳亚(Saul Luciano Lliuya)于2015年11月针对德国莱茵集团提起的诉讼。在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者(German watch)的支持下,柳亚提出要求德国莱茵集团提供21000美元财政捐款的诉讼主张,这些款项与修建防御冰川湖洪水、山体滑坡、淹没村庄和破坏财产的费用有关。21000美元相当于防止冰川湖洪水泛滥的工程项目成本的0.47%。该主张基于碳巨头研究而提出,即工业时代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0.47%可以追责到德国莱茵集团身上。
无论他们是否明确提及碳巨头研究,第二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中发起的诉讼都具体量化了碳排放公司单独的排放量和历史排放量,并基于被告的具体贡献进行辩论。例如,马林县、圣马特奥市和帝国海滩市的加利福尼亚地方政府在针对37家碳排放公司的诉讼中主张,被告作为化石燃料企业,“在1965年至2015年间直接造成227.6千兆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到这期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20.3%”。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证的气候科学和研究(例如希德对碳巨头的研究)的支持下,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公共当局方面很可能会继续代替遭受气候损害的当地社区提起气候变化诉讼。同样,公民可以依靠这种证据来请求法律变更。
3.归因科学的发展
尽管希德的工作帮助确定了单个被告或多个被告,但它并没有解决大额排放者是否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特定事件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不过,气候变化归因研究也在迅速发展。近年来,关于个别(极端)事件的归因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来自关怀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希德合作,将归因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通过追踪公司的长期排放情况,埃克沃泽尔(Ekwurzel)等人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大气温度的升高和海平面的升高归因于各个公司。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文章指出了如何将个别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死亡归因于气候变化,并最终归因于碳巨头企业。极端天气事件归因科学的持续发展有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与气候有关的诉讼的司法环境。
第二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已经得益于气候归因科学的进步,如果可以部分或集中地对因果关系进行科学证明,法院可能会更愿意接受公司承担气候损害责任。在柳亚诉德国莱茵集团(Lliuya v. RWE)一案中,德国哈姆民事高等法院驳回了埃森市法院(Essen Court)的判决,该判决基于原告无法确立具体因果关系而在一审中驳回了原告的主张。埃森市法院指出了驳回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让人回想起基瓦利纳的加利福尼亚地方法院,它认为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找到被告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原告位于秘鲁的住宅因冰川融化而受灾之间的明确因果关系。因此,原告未能满足德国民法规定的“如果没有”因果关系的标准。其次,它认为德国莱茵集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未能达到充分的检验,因为造成气候变化有许多共同因素。因此,不可能在单个实体的二氧化碳排放行为与具体的气候变化影响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相比之下,哈姆法院(Hamm Court)暂时接受了原告的因果关系论证,但要求在听证阶段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和专家意见。它宣称“虽然德国莱茵集团的排放并不是瓦拉斯(Huaraz)遭受洪灾威胁的全部原因,但足以就当前的排放量要求企业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负担部分责任”。因此,法院裁定,没有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要排除部分因果关系的存在,即可以认为德国莱茵集团是造成气候变化影响瓦拉斯的罪魁祸首之一。它还把气候模型视作有效的合法证据来源并得出结论,德国莱茵集团的排放是否对原告的家乡瓦拉斯造成了危害是一个科学判断。
在这个裁决之后,关怀科学家联盟声明:此类利用迅速发展的气候归因科学的诉讼,能让我们准确指出化石燃料生产商是如何造成海洋上升、全球温度升高以及其他后果的。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迅速地融入诉讼,突显了归因科学在战略性气候诉讼(尤其是私人气候诉讼)中的潜在关键作用。
(二)法律对话
前文所讨论的发展涉及的是科学知识的变化,让私人气候案件中的索赔人更易达到证据上的要求。通过结合气候科学、量化和归因科学方面的先进技术,索赔人现在能以可信度来主张:“如果没有X公司的排放,他们就不会遭受特定的、可估量的损害后果。”这种论点的扩散能让法庭上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表述不再是由无数未知和无法确定的来源引起的难解的普遍问题,而是由一群分散的、知情的行为者采取的一系列特定的选择和行动所造成的特定的、可估量的损害。这一概念化的结论会引发司法思维方式的转变,并将气候变化从政治问题转变为关心个体的问题。最近的诉讼已在表述上显示出细微变化。这种转变的两个突出表现是:(1)再次兴起了利用烟草和石棉诉讼判例价值的兴趣;(2)围绕董事责任和披露要求的讨论最近发生了变化。
1.扩大烟草和石棉诉讼的判例价值
基于侵权行为的第一波气候诉讼浪潮反映了一些在烟草和石棉诉讼中使用的策略。烟草和石棉诉讼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在英国的仙童诉格伦黑文(Fairchild v. Glenhaven)侵权案中,上议院确定了对原告有利的规则,原告在为不同雇主工作时接触了石棉,因而患上了间皮瘤。关于因果关系,法院认为,尽管不能查明是哪个雇主直接造成了损害,但被告格伦黑文公司仍在实质上增加了原告受到损害的风险,因此被判负连带责任。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烟草诉讼中的原告开始取得更大的成功。2002年,烟草诉讼中的个人原告在诉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一案中取得了重大胜利。陪审团认为,烟草公司有责任向贝蒂•布洛克(Betty Bullock)支付创纪录的280亿美元惩罚性赔偿,后者是一名64岁的女性,她因吸烟而患上了不可治愈的肺癌。最终在2011年,惩罚性赔偿金在上诉后降至2800万美元。
私人气候诉讼的困难与石棉和烟草诉讼的困难有许多相似之处。所有情况下的赔偿责任都涉及产品的生产(分别是石棉、烟草和化石燃料),最初这些产品被认为是无害的,但后来它们被认定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风险。由于存在多种因果关系,任何情况下的损害结果归因都变得复杂。此外,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处理石棉接触、烟草使用和气候变化的后果时都会产生大幅公共成本。然而,私人石棉和烟草诉讼的成功并未在第一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中得以复制。主要原因是在气候变化诉讼中建立因果链的困难更大。烟草和石棉受害者至少可以确认潜在的罪魁祸首,而第一波气候变化诉讼浪潮中的原告则无法轻易做到这一点。
不过,鉴于气候变化领域因果关系的变化背景,烟草和石棉判例可能对未来基于侵权提起的气候诉讼更具启发性。归因科学的发展让私人气候诉讼与石棉和烟草诉讼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气候诉讼的潜在被告群体正变得更容易被识别,并缩小到一个关键排放者范畴——“碳巨头”企业。此外,人们一直在努力证明,就像“大烟草公司”(big tobacco)那样,主要的碳排放者早就具备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和意识,却仍然采取了使公众困惑或误导公众的行动。在美国诉菲利普 • 莫里斯案(USA v. Philip Morris)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烟草案中,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凯斯勒作出了著名的裁定,司法部提供了用来证明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参与串谋欺骗公众的压倒性证据。因此,美国的经验表明,不仅直接受到影响的个体当事人可以起诉损害赔偿,政府也可以起诉公司以追偿与健康和环境损害有关的费用。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il)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也同样处于争议的中心,被指责压制气候变化研究,并在广告中散布误导性信息。
2017年7月,圣马特奥县、马林县和帝国海滩市在加利福尼亚提起的诉讼中,尝试在烟草和石棉诉讼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将其用作气候诉讼的司法先例。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烟草和石棉诉讼,加州气候诉讼的原告指控石油公司知道自己的排放活动正在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此外,政府作为索赔人在私人气候诉讼中的出现,有助于克服基瓦丽娜诉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科莫诉墨菲石油公司案中索赔人遇到的一些法律障碍。这些案件不是依据联邦普通法作出判决,因为在这些问题中,普通法被《清洁空气法》取代,因此不能适用联邦法院的普通法,而是以不受之前裁决影响的州普通法为基础。
烟草和石棉判例在强调私人气候诉讼的监管潜力方面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烟草和石棉诉讼证明,引入立法方案是一种改变公司行为的强大机制。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针对大公司的烟草和石棉集体诉讼数量之多,影响了以赔偿性基金和新的监管框架形式为内容的全面立法改革。尽管在身体暴露于污染状态与未来所受的健康损害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具有科学复杂性,法院并不总是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但石棉和烟草案件在为受害者提供系统性补救的立法计划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这种发展,可以预见在第二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中,尤其是在有关特定气候变化归因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气候诉讼有可能会推动立法变革。针对气候变化受害者的示范性立法计划提案已经在流传。正如道格拉斯•凯萨尔(Douglas Kysar)所预言的那样,尽管当前的美国侵权法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但私人气候诉讼数量的不断增长最终将迫使侵权体系去调整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并向与国家的监管角色保持一致的方向转变。
2.诉讼是公司气候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推动第二波战略性私人气候诉讼浪潮的另一处法律背景变化是,将诉讼作为公司气候风险管理的一部分。除了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可能提起侵权诉讼外,公司还面临着企业信息披露要求、董事相关职责以及股东和投资者要求提高气候风险敞口透明度的诉讼。特别是,关于能源密集型公司负有法律责任披露气候变化影响的论点,正逐渐成为诉讼的立足点。
气候风险披露已成为美国及其他地区诉讼的要点。2015年,纽约总检察长与皮博迪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 Corporation)达成和解,要求该公司披露在两年调查后完善的气候变化信息。由纽约州总检察长(及其他人员)领导的进一步调查集中在埃克森美孚存在在公司的气候风险方面误导投资者的可能。该调查与埃克森美孚公司资助那些反对气候科学组织的指控有关,与此同时,其公司内部的科学家向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阐述过潜在的气候风险。在英国,非政府组织地球正义(Client Earth)最近向财务报告委员会(FRC)投诉,指出两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SOCO International plc and Cairn Energy plc)的年度报告中遗漏了气候风险要素。
自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2015年9月发表讲话以来,公司董事因未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前景更加明确。卡尼警告说,公司董事和养老基金受托人可能要为人为气候变化负责,并为未能合理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在气候变化的商业风险方面误导投资者,或未遵守法律报告而承担法律责任。
在第二波私人气候诉讼中,股东就气候风险披露问题起诉金融服务公司的案例数量尽管不多,但意义重大,因此上述预测正逐渐得到证实。首例此类案件于2017年8月向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提起,恰好在其发布 2016 年年度报告之后。原告股东认为,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编写的报告未能将气候风险作为其风险管理框架的一部分,也未提及为昆士兰州Carmichael煤矿提供资金的问题。股东们要求宣布联邦银行违反了《公司法》,并要求其发布一项禁令,以防它在未来的年度报告中遗漏气候风险。一个月后,该案被撤销,因为联邦银行在其2017年年度报告中承认气候变化对其业务构成重大风险,并承诺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评估。
在气候投资者诉讼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应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与气候有关的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的任务是审查金融部门如何考虑气候相关问题,并加强“与气候相关的自愿且一致的财务披露,这将有助于投资者、贷方和保险承销商认识到其中的重大风险”。在2017年6月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发布的最终报告中,就G20管辖区范围内的企业披露气候变化相关财务风险的义务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指南。
同样,有人提议通过引入公司环境保护义务来改革公司法。这种义务类似于对渎职行为和普通法上的过失侵权行为(避免伤害他人的义务)的规范,并使公司披露和报告的义务成为强制性的。环保责任的核心思想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现代公司的宗旨和职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更具体的是,正如马西普鲁斯(Mathiopoulous)所说,重新定义现代公司的宗旨需要从以股东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转变为更广泛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模式,要求公司以公共利益和对社会与环境负责的方式行事。
这些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们代表着我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外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风险转变为需要适当管理公司的内部风险。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议事日程,需要通过从技术创新投资到制定披露策略、应急计划和保险等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些发展可能会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并减少在气候变化方面虚假宣传的可能性。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它们还可以减少未来气候诉讼的风险。
我们讨论的关键是,将气候变化风险视为企业风险的日趋成熟的理解为新类别的诉讼当事人打开了大门,这些诉讼当事人在确保公司作为负责任的气候风险管理者行事方面具有利害关系。现在,这一范围不再仅仅包括人们熟知的遭受气候变化损害的受害者和帮助他们的非政府组织,而且还包括股东和投资者,他们在获取所有企业资产和负债(包括与气候变化风险相关的负债)的全部信息方面享有既得利益。最后一类新当事人是公共机构,他们的利益在于确保公众不会被误导性信息所欺骗,以及确保公共资源不会因用于弥补气候变化损害而耗竭。这些都是新型参与者,他们也是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相比,例如成千上万在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席卷加勒比海和美国东南海岸线的风暴中失去了家园和财产的人,投资者、股东和公共当局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诉讼经验,并有更多的获取法律专业知识的途径。
(三)制度化和法制化背景
尽管绝大多数气候诉讼仍在美国进行,但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法院和其他审判机构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诉讼都在增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以外的法院出人意料地接受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种趋势在公共气候诉讼中最为明显,这一诉讼已经彻底地被乌尔干达案(Urgenda)的海牙地方法院和莱加里(Leghari)的拉合尔高等法院作出的裁决动摇了。
在私人气候诉讼中,法院最近也向原告发出了一些出人意料又鼓舞人心的信号。首先,关于菲律宾绿色和平组织的请愿书,在涉及 47 家投资者所有的碳排放企业的全国性调查中,人权委员会确认了其在侵犯人权的所有形式中拥有调查权和管辖权,包括气候变化造成的侵犯人权行为。这意味着委员会考虑了管辖权问题,并驳回了公司撤销调查的动议。委员会在2018年宣布了多个实况调查团和公开听证会,其中三个在马尼拉,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欧洲。请愿人在全球范围内呼吁两家公司参加公开听证会,并要求委员会在2018年12月10日(即《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成立70周年)之前向国家发布调查结果和决议。其次,哈姆地区法院最近在柳亚诉德国莱茵集团案中的裁决也给原告带来了新的前景,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因果关系等方面。
很难准确指出这些司法决策发生转变的确切原因,尤其是在荷兰和菲律宾这样不同的法律文化中。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随着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警告我们的地球正处于灾难性变化边缘的信号越来越多,我们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同样在南半球,也可以看出针对公司的气候诉讼的上升趋势。在菲律宾提出请愿书之后,其他几个东南部国家的居民,包括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图瓦卢、斐济和所罗门群岛,宣布他们打算提出类似的请愿书。同样,在柳亚诉德国莱茵集团案中,尽管涉及的赔偿金额较小,但认定被告的赔偿责任仍能产生深远影响。以下三个因素可以帮助解释这些最近的变化:(1)环境法庭的增多;(2)环境保护的宪法化;(3)跨国司法网络的建立。
1.环境法庭的增多
正如最近特别是南半球专业环境法院和法庭的激增所表明的那样,全球范围内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诉讼和裁决的增多,也许能部分归因于处理这些问题的司法能力在增强。在其他普通法国家,肯尼亚拥有可能有助于气候诉讼的法律规定,并设有专门的环境法庭。在印度,法官们一直愿意考虑环境损害可能对基本权利构成侵犯的主张。印度《宪法》第21条规定了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此外,印度拥有国家绿色法庭(NGT),自2010年成立以来,该法庭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决定,确认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权利。印度国家绿色法庭的决策程序非常活跃,并通过提供关键证据和数据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参与增强其权威。这标志着气候科学有可能在印度有关气候变化的未来法律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环境保护的宪法化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的宪法都伴随着一场“环境权利革命”,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通过人权和宪政的角度来解决。在196个拥有宪法的国家中,有148个国家奉行了某种形式的环境宪政。巴西、哥伦比亚、肯尼亚和墨西哥等106个国家/地区的宪法都承认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并承认检察官办公室在针对私人公司或政府行使这项权利方面的作用。这些宪法规定与不断完善的气候变化立法相结合,为气候诉讼提供了日益坚实的基础。
在巴西,联邦立法进一步规定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对环境违法行为的严格责任,这意味着没有必要证明被告因过失还是故意造成伤害。巴西高等法院依据这些法律规定禁止在甘蔗收割过程中使用火种,因为这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自从2009年国家气候变化法(第12187号)颁布以来,检察官办公室针对在圣保罗国际机场运营的40家飞机公司提起了集体诉讼,要求其承担降落和起飞期间造成排放污染的法律责任。目前此案正在联邦法院审理。
3.跨国司法网络的建立
国际法学界积极地教育国际和国内法院、法庭了解气候正义,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实现气候正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法律专家和法官于2015年起草的《全球气候变化义务奥斯陆原则》(the Oslo Principle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Obligations)确定了政府和企业(包括大型化石燃料和水泥公司)都有义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基础。其要求企业履行的义务包括:对脆弱性和风险的自我评估;对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客户,投资者和实体的公开披露义务;在建造新设施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企业气候义务专家组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法律专家和法官参与起草了《企业气候义务原则》。受《奥斯陆原则》启发,《企业原则》也规定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企业和投资者的气候义务,重点内容是减少排放。
五 迈向目标的尝试
总之,气候科学、法律对话和法制背景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一种向更有利于私人气候诉讼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归因科学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因果关系障碍,因为它们使原告更容易令人信服地主张,如果没有被告的行为,他们就不会受到环境损害。同样相关的是对话中的发展,它代表企业未能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不仅有负于气候变化的直接受害者,而且也有负于国家、投资者和股东。这种框架拓宽了新诉讼参与人的类别,这些新的诉讼参与人会带来气候变化受害者往往缺乏的特殊优势。投资者和股东可能比代表处于风险中的当地社区的非政府组织拥有更好的资源。公共当局原告也往往比典型的“第一波”原告拥有更多资源和经验,此外,他们能够援引个人原告无法获得的法律特权,例如“特殊关怀”考虑。此外,一些超出预期的,可以说是破例裁决的例子,例如乌尔干达和勒加里案,可能会鼓舞其他法院效仿。在宪法发展的背景下,突显出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民主法治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至关重要,这种环境可能正是司法部门所需要的,以便采取新的有争议的步骤,将减缓和管理气候变化重新定义为一种普遍的法律责任。
我们认为,本文讨论的科学、对话和宪法上的改变提高了当前和未来原告的胜诉概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并不是铁定的保证。例如在美国,政治问题和置换理论可能被证明不受大背景改变的影响。此外,即使原告更有信心地断言在会造成气候变化的选择和行为中,大公司应当对其中已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负责,这种归因形式可能仍然达不到司法预期,即特定的损害与确定责任的具体原因有关。确实,最近旧金山和奥克兰市针对5名公司被告人的诉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地方法院被驳回,因为法官认为气候变化的原因“遍及全球”,无法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各大公司迅速宣称,这意味着对于其余所有类似的诉讼大势已去。因此,尽管胜率有所提高,但第二波私人气候诉讼可能会遭遇与第一波案件相同的命运。
然而,环境诉讼的世界里充斥着代价高昂的胜诉和数量极多的败诉。原告并不总是需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为长期的法律变革作出贡献。事实上,现有的私人气候诉讼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动态:尽管还没有企业行为主体被追究法律责任,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催生了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法律和金融企业风险的概念,以及股东和投资者对企业将管理这种风险的相应预期。
涉及气候诉讼的被告公司很可能会因声誉受损而蒙受损失。即使被告公司成功地驳回了气候变化诉讼并收回了成本,其行为仍可能会受到持续的公众关注和财务审查。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公司在2017年将其AAA信用等级下调,随后面临投资者要求披露气候风险的压力。此外,当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在气候科学问题上积极误导投资者和公众的事实浮出水面时,其声誉受到损害。
此外还有诉讼费用。即使对于资源丰富的公司,气候变化诉讼的诉讼成本也很高。气候变化是一种跨界现象,有可能在任何发生气候损害的辖区对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因此公司可能会面临一系列诉讼。全球范围内的气候损害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着碳巨头公司可能要为现在和未来的气候损害付出数十亿美元的赔偿。此外,并非所有的气候变化损害都由保险公司承保。公司被告通常依靠责任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和辩护,但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针对公司的指控并不会自动触发保险公司对其客户的赔偿和辩护职责。
气候诉讼中更为广泛的其他领域也提供了一个不同但同样令人信服的提醒:不要将法庭上的结果与长期结果混为一谈。气候诉讼还包括旨在挑战气候变化法律法规的诉讼,例如欧洲法院裁决ETS航空的例证。在这个案件中,原告试图使欧盟的法律措施无效但未能成功,因为法院认为与航空有关的《排放交易指令》修正案是合法的。然而不到一年,欧盟决定暂停对第三国航空公司实施这一航空规定。结果欧洲法院的裁决并未解决欧盟、航空部门和非欧盟政府之间的争端,相反,它引起了轰动,并导致第三国对欧盟施加新的外交压力,并威胁欧盟对其实施贸易制裁,尽管这一制裁一直被这些国家视为不可接受的措施(无论是否受到司法制裁)。
ETS航空事业的事件表明,法庭上胜诉并不一定意味着胜诉方法的长期可持续性。此外,重要的是不要把判决的意义限制在其决定性部分。即使是在驳回原告请求时,法官也可以把裁决程序视作一个信号,强调法律变更的必要性,或是指出一种可能更容易实现败诉原告诉求的替代路径。正如在烟草和石棉诉讼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司法信号能通过对遭受损害者采取补救计划从而引发立法变更。最后,即使是缺乏这种司法推动力量,败诉案件也能促进社会变革。动物权利诉讼领域的例子在这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尽管未能在法庭上实现承认非人类动物是权利所有人,但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此类案件有助于提高社会意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态度,这种态度恰恰被证明在处理公共利益问题时比任何法律变化都更有效。
六 结语
本文通过讨论前述判例和未决案件揭示了通过诉讼追究温室气体大规模排放者对全球变暖的责任,或向工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诸策略的概观。该分析得出了一些关于私人气候诉讼现状的重要见解,并指出了此类诉讼在未来可能选取的方向。由于原告未能在气候损害与被告行为之间建立充分的因果关系,第一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很大程度上未能成功。然而,原告通过采用新的诉讼策略——利用气候科学的新进展,私人气候诉讼的势头正在增强。科学的发展、气候诉讼展开的法律对话和制度背景的变迁,极大地提高了原告在尚未裁决的和未来的气候变化诉讼中胜诉的可能性。
气候诉讼也已从美国扩大到整个亚洲、南美洲、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等其他新的司法管辖区。企业正在被调查其行为对人权的影响。来自南半球的公民正在起诉其各自辖区中的北半球公司。公民和民间社会行动者也越来越多地在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等南半球国家的司法管辖区采用创新的诉讼策略,这些国家更易接受基于权利的环境保护。
即使一家公司躲过了被气候变化受害者追究责任,它仍可能面临在未来气候损害、声誉受损、持续的公众审查方面的一系列责任成本和披露气候变化风险的压力。而且,政府可能会质询私营企业隐瞒公众和投资者气候变化及其风险的信息。此外,公司高管和董事可能会因违反考虑和披露气候变化风险的受托责任和义务而被直接起诉。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重新激发了关于私营企业的讨论,引发法律改革提案的提出,以重新定义现代企业的宗旨和职能。关于气候风险披露诉讼的案件数量会大大增加,并可能成为第二波气候变化诉讼的主要类别。
总之,尽管我们不能保证第二波私人气候诉讼浪潮一定会比第一波更成功,但胜算肯定有所提高。尽管过去的失败经历令人沮丧,但诉讼的激增表明,私人原告和维权组织正致力于在不断扩大的平台上继续追求新的诉讼策略。虽然这波势头不太可能让所有原告都取得胜利,但让法律无动于衷则更不可能。